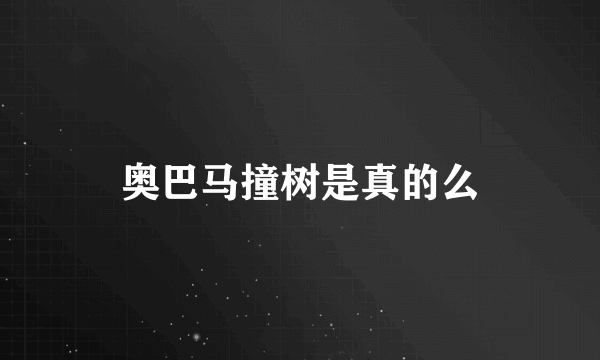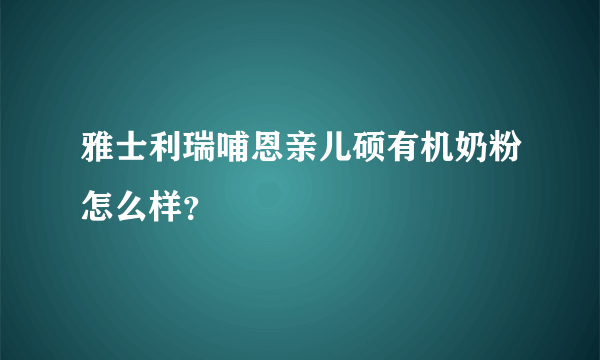赵若凡"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
偶尔看到一本儿童诗集《月亮生锈了》,作者赵若凡,是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。这本诗集之所以让人喜爱,完全因为它是天籁之声,记录的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自由的、无拘无束的想象。
也许是看到了月亮上的阴影,她想到可能是“月亮生锈了”,她想上去擦擦月亮,顺便上去逛逛。要换牙了,她觉得她的牙齿不想离开她,那牙齿甚至给她说“我要用502胶粘上你”。
小若凡的天真可爱之处,正在于她是个有心的孩子,她能很好地将看到的外部事物,和自己的内心世界联系在一起,构成令人们惊奇和欣喜的诗意与画面。有时你会觉得这些想象很“出格”,但这出格正是孩子大胆地、不受成人刻意与造作思维的干扰。在《天外来客》里,她想到飞碟闯入“我的家”,因为听不懂外星人说话,他要喝水,我却以为他想“尿尿”。她的想象有时十分狂放和张扬,在《让世界翻了天》里,她说自己想飞上宇宙,把“星球拽下/深入海里”然后“把鱼升上太空”“调动整个世界/让世界翻了天”。这让人想起哪吒闹海的故事,那个“闹海”的人,不也正是孩子吗!
若凡是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,在她的许多诗里,都表现出违拗父母意志的独立性格。在《对话》里,对于妈妈要她“晚上自己睡”,她说好吧,那我就不睡了。爸爸不让她用左手写字,她说好吧,那我“用右脚”。这真是有点故意捣乱,但这正是她独立思考的开始,是她想摆脱驯顺思维的可贵之处。
这些诗的可爱之处在于它完全是孩子的思维,没有成人理念的介入。其实,孩子的写作,应该保持它的原生态,像蓄满水珠的云朵,让雨点自己降落。我读过许多孩子的作品,明显经过成人的所谓“修改”和“加工”。你感到那雨水像是“人造雨”,极不自然,不时露出成人的“马脚”。
毕加索说起他的创作,说12岁之前,他向往大师,想向大师们学习,12岁之后,他就想向孩子学习。我想向孩子学习,大概就是想要保持一颗童心,一颗拥有天籁之声的心,保持永远成长着的饱满的创造力。
这本诗集里,还配有许多稚拙的图画,非常有趣,构图和色彩的大胆泼辣让人喜爱,这也是赵若凡的创作。
不错的好孩子。十二岁是一个复杂的年纪。女孩开始步入她的少女时代,然而孩子的蛹衣尚未完全褪去。细密的思虑像新发的枝桠,氤氲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忧伤。但这忧伤还不至于沉重到将枝桠压断,孩子的灵动赋予了它一种轻逸的特性,质地近乎是透明的,就像天空中最隐约的一朵云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,几乎不可能描摹出它的形状。所以属于这个年龄的珍贵而微妙的情感,总是稍纵即逝的,并且消失得不留痕迹。
赵若凡无疑是格外敏感的女孩,她用心地去感知着那些心情的变化。同时,她又有非常难得的理性,可以让自己从那种浸没的状态里跳脱出来,隔开一段距离去审视它们。那些瞬间的情感,被她视作璀璨的珍珠、耀眼的水晶以及灼艳的花朵,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。她将它们串结成珠链,编织成花环,存放进自己的妆匣里。一切自然而然,如同蜜蜂造蜜,似乎是出于一种本能。她毫无炫耀之心,甚至没有分享的意愿。这是属于她一个人的秘密。然而有一天,妆匣偶然被打开,当那些细软呈现在大家的眼前的时候,我们不禁惊讶于它们的光芒夺目。精巧、特别,引人入胜……一种慵懒的、漫不经心的天赋与才情展露无遗。
收录在《风般飘过》中的诗,既有现代诗,也有古体诗。对于我们这位年轻的作者来说,这种文体之间的转换好像丝毫不费力气。更多的时候,文体的选择并不掺杂技巧方面的考量,她只是将它们视作承载情感的容器。不同状态的情感应该用不同的容器来盛放。陶罐与瓷瓶,各有各的好,各有各的美。该选择哪个,作者显然得心应手。古体诗婉丽、幽邃,现代诗明艳、清洌,它们就像两个不同的房间,点着不同的灯,摆着不同的花,燃着不同的香,有着不同的氛围。然而,这两个房间又是比邻的,可以打开窗户让空气对流,——我们在古体诗里能读出一些现代气息,而在现代诗里又能找到几分古意。古意与现代气息很自然地融为一体。所以将这些不同文体的诗放在一本书里,读起来也觉得很自然,没有丝毫的突兀。
正如现代气息与古意的并存和交融一样,在这些形式多样的诗里,——几乎每一首,我们总是能感觉到一些彼此矛盾、互相对立的特质。这种奇妙的现象当然与所处年龄的状态有关,不过也是作者身上天性的呈现。她的显耀才华正是植根于这样复杂的天性的。质朴与华丽、理性与抒情、疏离与沉浸、沧桑与纯真、稚拙与精巧。它们的并存和对峙构成了诗歌内在的张力。悉心甄选的词语灵巧地在这些对立特质之间跳跃,创造出奇特的语境,而词语本身也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,常常会有让人心头一震,微感惊愕的感觉。如何能让一个词语发挥出它最大的并且是全新的效能,显然已经成为作者开始思考的问题。如果说,在词语方面,作者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自觉性,那么在节奏方面,作者则完全是出于本能。如何停顿,怎样转折,什么地方终止,都是凭借直觉来作判断的。令人赞叹的是,在大多数时候,它们都显得自然而准确。重复也是作者多次用到的修辞方式,在其中我们同样能感觉到对韵律的控制,然而又不仅仅是流于形式表面,它同时使情感表达得到升华,有一种怅惘、呓喃的感觉。
鲜明的、令人难忘的意象常常是诗歌的灵魂所在。在这本小诗中,有些意象反复出现。比如“梦”。“梦”喻指的也许是飘渺的情感,也许是致幻的体验,又或者是一切无法抓住的美好事物。然而,在这些作者最初创作的诗歌里,“梦”可能是更大的东西,它也许就是诗本身。正如诗人保罗.瓦雷里所说的那样,界定诗的世界与梦的世界有着许多相似之处。就是说,做梦与诗在我们心中形成、展开、最终消失的过程很像,“它们都是不稳定的、变化无常的、不由自主的、易消逝的,我们会偶尔失之,正如我们会偶尔得之那样。”所以,当“梦”的意象一次又一次出现,作者似乎是在邀请读者走进她的“梦”里,而梦境即诗境,
其实也是她此刻所处的创作状态。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“梦”的意象显得格外特别,充满感染力,带给我们一种强烈的代入感。这些诗里还有许多别的意象,它们和“梦”一样,对描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,都是向内的,指向作者本人的。事实上,通过这些意象所传达出来的那种“将世界隔绝在外,完全无视它的存在”的姿态,或许正是这些诗的一个迷人之处吧。
我猜想或许要到很多年以后,若凡自己才能真正意识到这些心情的细软是多么珍贵的财富。对于现在的她而言,创作的过程或许比这些诗歌本身更有价值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,能够读到这样一些神采飞扬的诗作,能够如此真切地体会到“梦”的状态,实在是非常美好的经验。
那么,你准备好了吗,现在就打开若凡的妆匣吧——
(《心情的细软》张悦然)
赵若凡是个小诗人,8岁出版诗集《月亮生锈了》,12岁出版诗集《风般飘过》。
我和她一个学校的,没听说这些啊。她在学校挺低调的,不怎么爱说话,感觉就是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况且别人上节目、出书,那也要她有那个本事啊。我反正是没有。
人赵若凡,学习好,班干部,有文采,总是容易引人羡慕妒忌恨啊,看来人怕出名啊